孤魂野鬼(4)
2022年03月29日 作者:鬼怪屋 来源:鬼怪屋故事网 民间异闻
听了这话,她却变色了,回道,此生都愿在家奉养叔嫂,若一定要她出嫁,宁可出家做尼姑去。
长辈以为她说笑,他却深知她执拗的性子,绝不会无缘无故说这样的孟浪话。可是无论如何试探相问,她都不肯做答,只云和家人相处惯了,不爱出去。
他心里甚明,却不知该如何向父母开口。
父母早就打定主意要为他寻门当户对的亲事,以保自家数代的基业。断不肯娶她做妻的,她父母早亡,无亲无故,能多年照顾她已是尽到心意。
可他心里却也舍不得她,眼见她日渐清减,整个人憔悴得风吹便倒似的。
终于忍不住,他跪倒在父母面前相求。
他俩从小的情形,父母都看在眼里,岂有不知之理。只是这么大的基业,怎么肯胡乱许亲?
他跪地良久,父亲终于道,假如她也愿意,便做了小吧。
原本,父母不愿委屈她,欲为她寻一良配,风光体面地出嫁,也省得惹外人口舌,说他们亏待了兄长留下的孤女。
他得了这个令,却不知如何向她开口,那句话在嘴里绕来绕去总是吐不出去。
她却早已从丫鬟处得到消息,一见他来,便道,“我愿意。”
他忍不住便泪下,两人相对无言,唯有泪千行。
她身子便逐渐好起来。
两人偶尔也在诺大的王府花园游走。她每至一处便会停留甚久,说起当日的情形,神色哀怨。
他便劝慰以后天长日久,何必只日日沉思往事?
她却不听,怕他忘记似的一提再提。
他只得笑着听着,心里却总有不详的预感。
翌年春天,他的婚事终是议定了。对方是淮南王的次女,美名在外,据说是淮南第一美女。
她听了,便笑着向他道,“这第一美女不知如何美法,我跟她比,怕只能当小丫鬟了。”
他握住她的嘴,假意斥道,“别乱讲,谁也比不上你美。”
婚事定在夏末,他必须赶赴淮南迎亲。
出发之前她却要他作画,“我觉得这会儿精神好,以后不知还有没有这样的时机,你便好好画我吧。”
她穿了一袭粉红的薄衫,就倚在荷塘边的软塌上,手腕上的朱砂痣鲜红欲滴。
彼时荷花亭亭玉立,塘边古树浓茵如盖。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可是这荷花的艳却不及你半分!”他笑着对她说道,心里是无穷无尽的蜜意。
她莞尔一笑,刹那间神光四射,这绝世容光使得荷花都不禁低了头。
这一次迎亲来回走了一月。
他焦灼异常,偏生这么多的繁文缛节,偏生这新娘有这么多的亲戚他需一一结识。
可是他心不在焉,最后连新娘父亲淮南王的眉目都没记清。
他终于回来了。
那日钱塘王府张灯结彩、锣鼓震天。
他被按在席上无法脱身,究竟喝了多少酒都不记得,只记得自己来者不拒,只求少些聒噪。
他念着自己终于有妻了,有一个人以后将生生地插在他们之间,和她再也无法似过去般亲密。
一直闹到深夜,众人把他送到新房终于一哄散去,他连新娘的盖头都没掀就奔了出去。
终于步履踉跄地奔到她的屋子外,他重重地扑了门上。
已是夏末,屋外的荷塘荷花已经开败,只剩几杆枯枝兀然立着。
良久,只听得她轻盈得脚步声行到门前,低低地问是谁?
他含混不清地道,快开门快开门。
她开了门,身上仅着亵衣,俏生生的立着。脸上先是惊鄂,接着便是欢喜。
他直扑进去,一把便揽她入怀,顺手关了门。
他在她耳边呢喃,“离了你才知心里有多惦记你,这一月里我魂不守舍,巴不得早点飞回来见你。”
两人俱是满心欢喜。
她欲开口,他却用嘴堵住了她的嘴,打横抱起她滚入床帏。
他们第一次这样赤裸相对,她羞涩地不知如何应对,醉了酒的他却只知一味的掠夺。
她吃痛不过,呻吟出声。
……
林少卿沉浸在往事里,直到胡不归走到身边才惊觉。
胡不归双目肿得跟个桃子似的,林少卿一想到这眼泪是为陆蓝江而流,心里就一阵剧痛。
胡不归道,“我要去寻陆蓝江。”语声虽低,却透着无比的坚决。
“天下这么大,你又去哪里找?”林少卿背转身子。
“总好过在这里等死,这一生,假如不能见他一面,我怕是死也无法安心。我不敢相求你帮忙去寻,你只需告诉我他大概去了哪里。”
林少卿沉默半响,终于道,“你一孤身女子,哑叔出门不方便,小夜又不懂事,我怎么放心?”
“那你是要陪我去么?”胡不归有隐约的喜色。
林少卿长叹一口气,终于应道,“我自然陪你去。”
次日一早小夜便来催林少卿动身。
林宝却还未归来,林少卿便写了一封书信留在书案上。
出得门来,哑叔已拉着马车等在门前。
那马不知多久未曾上路,早已老态龙钟。
胡不归和小夜上了马车,哑叔也执着鞭子坐在车辕上。
林少卿见那马不堪重负的模样,便拒绝了哑仆的好意,抬步便走,反而是马车隆隆地跟在身后。
出了林子,便是大路。
林少卿早已和胡不归议定先去苏州,因陆蓝江尚记得苏州乃是故居,怕是再度回去也未可知。
这一路两人俱是心事重重,哑叔又不会说话,倒让小夜一人生出许多闲气来。原以为总算出了蜗居那么久的宅子,总能遇见些新鲜物事,日日相对的是却是林少卿和胡不归的长吁短叹。
难得有人欲打破僵局,说上一句话,对方却又厌厌的。
“真是古道西风瘦马,断肠人在天涯。”那日在路边进些饮食,林少卿忽然望着路边的枯藤老树便道。
胡不归却不抬头,只低低唔了一声。
隔日借宿一间乡间大宅,胡不归道,“这宅子倒似我们的宅子,我总想着明年你能在那里看到荷花怒放。”言毕,自己也觉不妥,林少卿也不作答,只微微点了点头。
慢慢接近苏州,沿途便繁华起来,时时有大群人呼啸而过,鲜衣怒马,似是富贵人家出游。
胡不归便甚少露面,四人之间更是默默。
那日终于行到苏州城外,远远地望着巍峨的城门,林少卿心里有些微微的苦涩。
偏偏胡不归喜悦的声音又从车内传出,“终于到了苏州了么?”语声细软,和她从前低低的哀音大不相同,吴侬软语的娇俏之意尽显无疑。
林少卿微微叹了口气,她终于没把我放在心上么?
苏州城自是繁华无比,车如流水马如龙,四人好不容易才行到西郊原先胡家的旧址。
触目处却依旧是一片焦黑,断壁残垣,说不出的凄凉。
胡不归心下黯然,默默低头垂泪。
林少卿强自欢笑,劝慰道,“这也是没法子的,别伤神了,对身子也不好。”
四人正默默间,忽然有人飞奔而至。
衣衫褴褛、面目漆黑,却只剩一双眼睛仍旧是乌黑灵活,不是林宝是谁?
林宝在林少卿面前扑通跪下,两行眼泪立时涌出,在他乌黑的脸上划出了两道细流。“少爷啊,您再不来,林宝要饿死了。”
四人惊异不已。
原来林宝那日离了大宅,也不由便往苏州去了。可走的匆忙,忘了带些盘缠,走了几日便身无分文。却又不欲再去乞食,于是抄小路折返大宅。也因为走了小路,便与林少卿一行错失了,到了大宅扑了空,便再次追出来。他一人脚程甚快,又每每走些僻静小路,倒比林少卿先到了苏州。只是这一路上风餐露宿、半饥半饱,倒真吃了不少苦。
林宝号啕大哭,林少卿只好由着他扯着自己衣服下摆,倒把鼻涕、眼泪都胡乱擦到了他衣服上。
终于等林宝哭得畅快了,又吃了小夜赶紧去买来的馒头,林少卿才可以好好的问话。
林宝早到这几日却也不是白到,他四处去打探,倒真探问到不少消息,“这街坊四邻还真有人见过陆公子。前边街拐角的那个婆婆就说见过陆公子,我们一起再去问问好了。”
五人走到街角,果然有一位卖馄饨的老婆子,边上还摆着几付破旧的桌椅,生意看来甚是清淡,都是路过的行人却无人驻足。
林宝抢着替林少卿用脏脏的衣袖擦了擦长凳,小夜也不甘示弱,替胡不归打点了一切,还垫了一块薄毛毯。林宝便有些愤愤。
那老婆子见来了这么多客人,便欢天喜地地走近,招呼道,“可是要来五碗馄饨么?话音未落,那老婆子便直视着胡不归惊叫起来,“胡小姐?你是……是……是鬼么?”两股战战,却挪不开步去。
小夜愤然起身,怒斥道,“你这婆子瞎说什么?我们小姐好端端的是人。当日胡家是被大火烧尽,可是我们小姐正好去了寒山寺没在家中,怎么会是鬼?”
老婆子惊魂不定,眼珠乱转打量着其他人。
林少卿却拿出一锭银子,足有五两重,漫不经心地扔到桌上,道,“老人家别多疑,我们只是跟你打听个事情,这锭银子先收着。”
见了银子,老婆子总算定了神。
“可曾见过陆蓝江公子?”胡不归急急问道。
“半个月前,我见到一位模样俊俏的公子在这边走来走去,若不是脸上那道伤疤,我肯定一见就认出来了,后来又见了好一次,才敢确认是陆公子。”
“他可曾与你说过些什么?”
“他是找我问,说这间大屋怎么就被火烧了?我说被天雷击中就烧了。他又问这家里的人去哪里了?我说都烧死了。”言毕,老婆子又急急辩解,“我委实不知道小姐你死里逃生啊!这怪不得我啊。”
“那陆公子后来去了哪里?”
老婆子掐指一算,“陆公子来了三次,前两次都只是乱走,还不时敲自己的头。第三次才来问我。问了以后就走了,再没来过。”
“陆公子还说什么没有?”
“陆公子倒是没再说什么,倒是我见陆公子脸上的伤疤很是好奇,还多问了几句。”
“那陆公子怎么说?”
“陆公子先是很不情愿,后来却终于说是路上遇着盗贼了。我又问怎么这么多年才回转,胡家小姐都一直不肯出嫁。这么一说,陆公子却又糊涂起来,就自去了。”
胡不归一脸失落,清凉的眸子慢慢模糊起来。
林少卿又扔出一锭约莫二两的银子,便起身道,“我们走吧!”
那老婆子又得意外之财,乐得两眼都直了。回过神来,那五人却已走了有十步远了,心念一动,连忙喊道,“那陆公子走时,我听到他嘴里好象念着什么,好象是什么荷花什么桂花的!”
胡不归霍然转身,道,“可是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她记得,她当然记得。两人读到“三秋桂子,十里荷花”这句词时,都心生向往之意,约定总得找个时机去一次,去看看美绝天下的西子湖。
老婆子连连点头。
“走吧,我们去杭州吧。”胡不归举步便走,小夜急急跟上。
林少卿却又仿佛失了神,喃喃道,“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新婚洞房之夜,他借着酒胆抛下明媒正娶的妻,沉醉在她的温柔气息里,两人一直痴缠到天明,雄鸡报晓了都浑然不觉。他完全把妻抛在脑后,忘了那个独守空房的淮南第一美人。
他知道,她是最懂他的,所以他也必须最珍惜她。
可是他的妻,淮南王娇纵的女儿怎么肯受这样的屈辱?
次日清晨父母便得了信,知道他竟然夜宿她处,连妻的红头盖都未揭。父亲赶紧着人来唤他,他才有些警醒,手忙脚乱地便赶了去。她不放心,便也跟了去。
父亲铁青了脸,一语不发。母亲却只在一边垂泪。两人惶惑不安,只得跪下。
父亲终于开口,对他言道,“你如今也大了,有自己的主张了。我只提醒你一次,你得记着,你房里的是你堂堂正正的妻子如意,是以后的钱塘王妃。你可以纳妾,但是她才是你的妻,你必须敬她爱她,不能委屈她半分。”
他诺诺应着,却感觉身旁的她摇摇欲坠。
父亲却没轻易放过她,又对她言道,“我家待你总算不薄,也盼你懂事些,如此这般胡闹,我怎么对淮南王交代?”
他正欲分辨,她却以目光止住了他,道,“错在我,以后再不敢这般胡闹了。”
父亲却再不语言。
母亲忙对他道,“还不快去新房,媳妇等了你一夜了。”
他慢慢起身,回头看她一眼,她依旧跪在地上,哀哀地低着头。
他缓缓走回新房,心里如一团乱麻。
他曾经以为娶回一个妻以礼相待就是了,如今却发现自己心里再也放不进另外一个人,他满心满眼全是她,连看别人一眼都不愿意。
他推门进去,那门仿佛千均之重,他几乎无力推开。
新房里红烛早已燃尽,长长的烛泪一直蜿蜒而下,在桌上堆成一滩,若不细看,几乎便以为那是鲜艳的血。
如意却端坐在床沿,听见他进门的声音依旧一动不动。
那凤冠霞帔红得刺眼,身上更是珠光宝气,几乎照得一室生辉。头盖上绣着的是鸳鸯戏水,两只鸳鸯憨态可拘,它们只知一心一意对待对方,怎知世人的不如意?
他呆立半响,终于挑起了那块红盖头。
如意竟然对他展颜一笑,明眸皓齿、肌肤胜雪,那一笑宛如风过春水,荡起层层涟漪,绵绵不尽。
他有片刻的失神,心里有些微歉意。
“相公,听闻你昨晚醉酒,醉卧在了花厅,不知今日好些没?”
他有些尴尬,父母是要他瞒住如意,“真对不住,昨夜被灌多了酒。你怎么就坐了一夜,太辛苦你了。”
如意却依旧微笑着,“我怎么能自行揭去红盖头,等相公是理应的。”
梳洗过后,如意随他出来拜见父母,她也来了。母亲却拦在他前头,赶紧说这是他表妹,从小长在他家,和他情同兄妹。
如意不疑有它,便亲热地执了她手唤了声妹妹。她也微微笑着,福了一福,唤了声表嫂。
他在一边望着,手心里都捏出冷汗来。
是夜,他终于宿在了新房,只是面对眼前这娇艳如花的新娘,他却始终不肯睁开眼睛。
触手处柔软光滑,却不是他想要的那一个……
春xiao苦短,他却早起了,他知道她此刻必定在荷塘边。
远远望去,她单薄的身影陷在薄薄的晨雾里,仿佛随时都可化去。
她听到了他的脚步声,低声道,“这便是秋天了,我瞧着园里的桂花怕快开了。”
他低低应了声,满心想给她些安慰,却不知该说些什么好。
她仿佛知他心意一般,转过头来,浅浅一笑,“不用说什么,你的心意我都明白。我什
么都不怨,能守在你身边看着你便已是心满意足。
他说不出话来,只执了她手,两人痴痴相望。
两人皆是小心翼翼,在如意面前彬彬有礼。
只是两人却不知正经的兄妹是怎么处的,只想着两人生分一些,即便三人一起在院中散
步,他们俩中定然有一人落后一丈之远。偶而也说话,却从来避开对方的眼光。
如意自然不是呆子,慢慢地神色却也变了。
世上到底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么大一家子总有几个奴才嘴风不紧,甚至还有刁钻的奴才
故意漏些口风,盼看场好戏。等他知道大事不好的时候,她的贴身侍婢玉兰已被如意请了去。
他急急赶去时,玉兰正瑟瑟地站着。
如意却袖着手,施施然地坐在椅子上,手里还执了一柄团扇,无事人一般轻轻摇着。
见他来了,如意便立起身来,向他福了一福,说道,“我听闻奴才之间有些不堪入耳的秽言秽语,涉及妹妹清誉,我便唤来玉兰问一问,可知是什么狗奴才这么大胆散布这样的谣言?”
他讷讷不能言,——她要做我的妾的——这句话在心里滚来滚去,终是没忍心说出来,他毕竟是欠如意的。
如意见他不做声,便道,“或许我是管得宽了些,但是初见这个妹妹便特别投缘,实在不愿这些脏话白白玷污了她。要是这些话传到外面去,妹妹还怎么嫁人啊?”
这话说得他心里一惊,原来如意心里打得竟是这个主意么?
这时她却赶到了,见到玉兰没半点损伤才放了心,方才问道,“表嫂叫玉兰来做什么?”
如意搁了团扇,走到她身边,执了她手握着,道,“妹妹,你不知道姐姐有多喜欢你。我家里只有兄长,从来没见过这么聪明美丽的姐妹,心里喜欢得不得了。姐姐多么盼望妹妹以后嫁一户好人家,像我这般。偏生有些刁奴总爱搬弄是非,姐姐气不过才找玉兰来问一问。”
“这又干玉兰什么事了?”她甚是气苦,脸色也微微变了。
“玉兰是妹妹的贴心人,我也是想问她一下妹妹的心意。总之,妹妹你放心,以后有姐姐在,总不让妹妹吃苦。”
她略略挣了一下手,却没挣脱。
“说起来,我家中还兄长未曾娶亲的,不知道说与妹妹可好?”如意的脸更凑近一些,细细看着她的神色。
她泫然欲泣,却拼命忍着那泪,他知道她不愿在外人面前示弱。
他已忍不住,她却哀哀地看着他,微微地摇头,他只得又把话咽回去。
一场闹剧倒也和平收场,父母把他俩唤了去,又是郑重叮嘱一番,道是纳妾之事总得稍后再议,不能委屈了如意。
两人走出正厅时,天色已晚,天边一轮红彤彤的太阳正慢慢下坠,却忽然闻见传来暗暗的桂花香气,若有若无,又丝丝不绝。
两人停了步子,这桂花香便慢慢浓起来,似乎覆在了两人身上,沁人心脾。
“月缺霜浓细蕊乾,此花无属桂堂仙。鹫峰子落惊前夜,蟾窟枝空记昔年。”他慢慢吟道。
“这桂花就好在清净,总不会让人腻烦。”
他回首俯视着她,低低笑道,“你难道不知道,我爱你也是这点么?”
她微微一笑,缓缓说道,“不管多久,我总是等着。”
他凝神看着她眼里的坚决,道,“不管多久,我心里只有你一个。”
林宝见那老马赢弱不堪,便很不屑,撇撇嘴道,“这样的马也可以上路?少爷,我们去
买匹好马吧,走在路上也威风一些。”
林宝终究是小孩脾性,林少卿却盼着这路走得愈慢愈好,走不到尽头才好,就这样一路相随,偶尔有只言片语,便足以心安。
林宝见林少卿未反对,便自作主张买了三匹马,连马车也换了一辆新鲜光亮的,更是给自己添置了新衣,简直不似个书童了。
小夜便嘲笑他道,“你简直不把你家少爷的银子当银子花。”
林宝却理直气壮地回道,“我家少爷说了,钱财这些东西全是身外物。所以我林宝该花就花。”林少卿听了却也只微微一笑。
只是自此,林少卿便只能与林宝骑了马,再不能跟随车右。
这一次速度甚快,只两日便到了杭州。
宋代赵构曾在杭州建都,文人墨客对西子湖的称诵更是数不胜数。时虽已是隆冬,游人依然如织。
林少卿五人一达杭州,杭州便下起大雪来,飘飘洒洒,一时间天地万物都被笼罩,倒显得这红尘俗世分外干净。
五人也不急于找店住宿,便先赶到了西子湖边。
远山早已模糊在雪色里,近处仍可见碧波荡漾。那绿意与别处不同,别有一番柔媚在里头,仿佛杭州盛产的丝绸一般,光滑细腻。
林宝和小夜是一心一意地看着雪中西湖,胡不归却念着陆蓝江这样的文人雅士也许会来西湖边赏玩雪景。
天气极寒,胡不归穿了件雪白的狐裘大衣,越发衬得她眉目如画。
林少卿隔着她两三丈远慢慢跟着,楞楞地望着,似是痴了。
胡不归浑然不觉,只焦急地四处打量。雪已经积得有两三寸厚,踩在上面咯吱咯吱地响,溶化的雪水微微渗入,她似乎无知无觉。
湖边行人不少,皆是些赏雪的风雅之士,也有一些富家小姐远远地立着,边上围着丫鬟、奴仆,以防生人接近。像胡不归这般着急走路,东张西望地却很希奇,早已惹得旁人对她指指点点。
林少卿却也尴尬,不知是上前陪护好,还是在后紧随好。再去看那小夜,正和林宝吵闹得高兴,两人互扔着雪球玩。
林少卿正自彷徨间,眼看着马上即到断桥,忽见前面来了一大队人马。
为首的公子骑着一匹高头大马,那马浑身雪白,没有一丝杂色,偏偏四个蹄子上却是纯正的黑色。马上的公子更是丰神如玉,一身锦绣,头上带着束发金冠。
公子的身后跟着十数位家丁。一群人甚是张狂,旁人见了纷纷避让。
林少卿神色变了变,仔细打量着那公子,却对胡不归失了照顾。
耳听着扑通一声,小夜惊叫出声,转眼望去胡不归便没了踪影。
原来是那路人马走近,胡不归为了避让,脚下一错步,竟然失足跌下湖去。
林少卿急奔至岸边,胡不归正在水里挣扎,可是身上的狐裘大衣吸了水便得分外沉重,一寸一寸地把她往水下拉。
林少卿面如土色,正欲往水中跳去,却有一人抢在他头里跳了下去。仔细一看,竟然是那锦衣公子,林少卿不由楞在当地。
林宝已经赶上前来,急急拉住林少卿,道,“少爷,你会水么?”
林少卿木然答道,“不会。”
林宝连忙又紧了紧拉住林少卿的手,道,“千万不能跳,你不会水,现在又天寒地冻的,就算不淹死也冻死了。”
那锦衣公子身手却甚是矫健,三两下便拉住了胡不归望岸边拖过来。那一众家丁赶紧上前,接过手来,便把锦衣公子和胡不归拖到岸上。
两人俱已湿透,胡不归已然晕厥,紧闭着双目,面色青紫。
林少卿欲上前探看,却被一众家丁拦在一边。小夜喊着小姐直扑过去,却也被拦住了。
林少卿心里惊魂不定,却见着那锦衣公子转过脸来,双唇青紫,目光凛然,语气清晰地道,“人是我救的,那自然就归我了。”说罢便抱起胡不归跨上了白马,呼啸而去。
四人面面相觑,小夜早已忍不住,号啕大哭起来。
旁人希奇地看了他们几眼,便逐渐散去。
孤魂野鬼
部分文章源自网友投稿或网络,如有不妥请告知,我们将在24小时内修改或删除。
如果您有故事想与鬼友们分享,请将稿件发送至编辑邮箱:ra216@qq.com



![[短篇怪谈]富人郑胖子因强拆命案被送水工复仇,妻女相继惨死,诡异水杯引出惊悚真相](https://img.picgo.net/2024/07/13/36dd328b12bddd76e8.jpg)
![[短篇怪谈]村民某甲轻薄女子,遭遇骷髅头怪惩诫,从此惊恐悔改,成为规矩人](https://img.picgo.net/2024/06/24/7938be45a8e93f8d67.png)
![[短篇怪谈]五层楼谜案:迷局复仇与失忆罪恶的代价](https://img.picgo.net/2024/06/24/4146218d8a3d3d538b.png)
![[家有鬼事]悼亡魂](/UploadFiles/2023-10/2/2023102015195734153_S.jpg)
![[短篇怪谈]同学聚会,男子酒后遇诡异,山林险境,遭遇狼群袭击,生死搏斗,揭示惊人真相](https://img.picgo.net/2024/06/24/2687d9315eb213da45.png)
![[短篇怪谈]短发女生的诡异游戏:毕业照中的幽灵之谜](https://img.picgo.net/2024/06/13/13d6b12117f2bb7c9e.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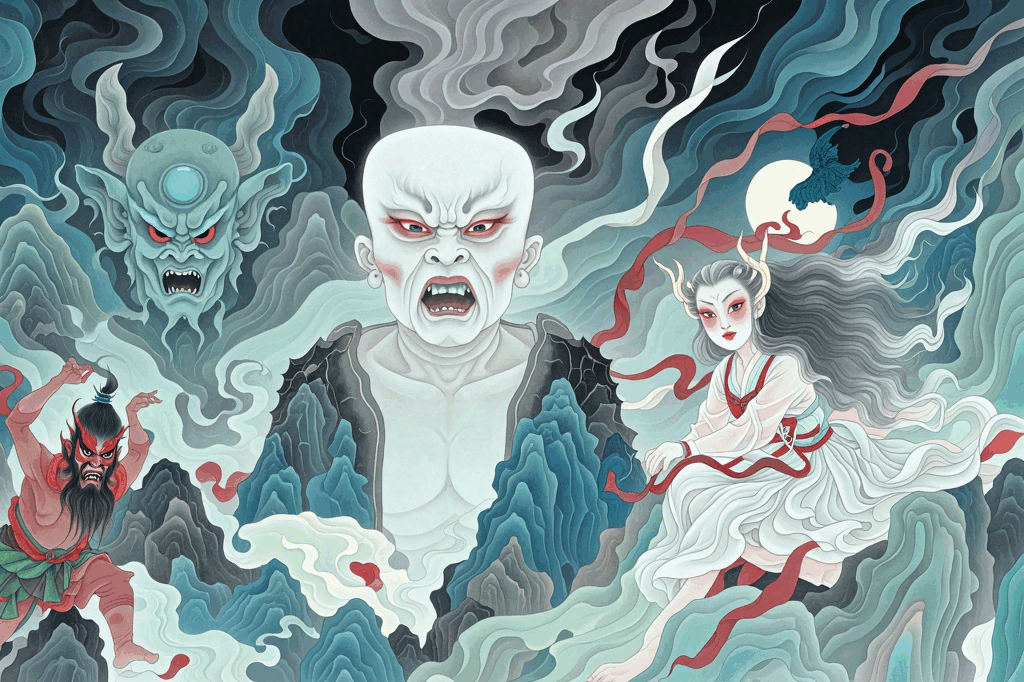
![[中短篇灵异小说集]23个极短的恐怖小故事](/UploadFiles/2023-08/2/2023082414375073692.jpg)
![[中短篇灵异小说集]经典鬼故事大全](/UploadFiles/2023-08/2/2023082414334270430.jpg)
![[中短篇灵异小说集]八十年代农村灵异事件](/UploadFiles/2023-08/2/2023082414292368407.jpg)
![[中短篇灵异小说集]让人不敢睡觉的鬼故事](/UploadFiles/2023-08/2/2023082414241432785.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