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彤鬼故事系列:诡异工地
2022年04月25日 作者:鬼怪屋 来源:鬼怪屋故事网 短篇怪谈已有158鬼友看过
序言
二零零八年春节以前,我一直在北京某大型建筑公司任保安队长一职,屈指算来已经近八年了。八年里,我随着公司南征北战,西至河北易县;南至天津塘沽;东至河北承德;北至河北张家口,前前后后一共干了七十三个大小不等的工地。
八年来,在我所管辖的某些工地里发生了许多匪夷所思的事件。
今年我已经脱离了施工现场的保安工作,所以也不怕得罪建筑行业的鼻祖——鲁班祖师爷了。
在这里,把我亲身经历隐藏心中很久的其中的一件事和大家说说,共讨之。
二零零三年四月,闻之色变的“非典”在大肆肆虐广州等大城市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刮进了北京城城。
一时间,整个北京城风声鹤唳,口罩、84消毒液、板蓝根冲剂等物品、药品被一抢而空。熙熙攘攘的街道、拥挤不堪的地铁、车水马龙的二、三、四环、人头攒动的“鬼街”、游人如织的故宫……全部变得门可罗雀、冷冷清清,记忆最深的是我有次开车从万寿路上西三环去通州,车从玉泉营至洋桥的三环主路上,只有我一辆车,以为是交通管制,所以在洋桥赶紧驶出主路。
外地的施工现场已经不能再去。临近北京的外地郊区县纷纷设卡、断路千方百计的二十四小时不间断阻止从北京方向来的车辆出京。
当时在北京朝阳、宣武、丰台、海淀、石景山几个区内,我单位还有十一个工地,八十六名保安、三百多现场管理人员、七千多民工。
市政府以张贴告示、下发通知、宣传册等各种形式来阻止在京的外地人员返乡,以免给国内未爆发非典的城市乡村带去灭顶之灾。
当时,我公司总部设在万寿路。依据公司领导指示:各现场要继续施工,为安定军心,公司组织专人去外地采购中药,同时要求各现场要加强封闭管理,尽量减少外来人员,每日早晚测体温、加大宿舍空间,注意合理饮食等指示精神。其中关于加强现场管理一项责无旁贷落在我的肩上。
说实话,我也害怕。从不带口罩到带上一个口罩、带上两个口罩出门先后没过三天。
还有,我小时候就怕打针吃药,只要没到躺床非到医院不可的时候我绝不会主动去,但这次我带头一天两袋捏着鼻子喝那能把你苦晕过去的中药汤剂。
没办法,硬着头皮也得上,谁让咱是保安队长、党员呢!
公司专门给公司保卫部配了一辆金杯车,我专门成立了个巡查小组,每天不分昼夜带着一个处突小组到各现场去巡视检查。
市政府为了防止疫情扩散,特地在各区医院都设置了发烧门诊,同时指定了许多发烧医院,其中应该是以小汤山最为有名。
以讹传讹,小汤山被人们传说成“死亡之地”,只要拉到那去,必死无疑。
这个传言使工地的民工异常恐慌,从开始的消极怠工、群心骚动逐渐演变成“北京大逃亡”。夜深人静的时候,民工们三五成群有计划、有组织的拆围墙、跳大门,一心一意想回到家乡。害的我是一天到晚频接警报,现场保安东围西堵、疲惫不堪。
我在宣武区某工地曾亲手抓住过跳墙的民工,无论你咋劝说,他们只有一个动作、一个语言。
把他们逼急了他们“噗通”跪在地上,磕头如捣蒜,只有一句话。
“求求你行行好,放我回去吧,死我也要死在家乡,不能被拉到小汤山上烧了!”
五月的一天凌晨。
我带着巡查小组来到位于良乡大学城的某个工地。
这个大学城是响应北京市的号召在零二年开始规划建造的,市区内的多所大学将来都要搬迁到这里。
我公司承包了某一大学钟楼、教研楼、图书楼、计算机楼的建筑工作,建筑面积有近二十万平米。工地四周被围挡严实挡住,只留有向东的一个大门,以一个大大的南北走向的“逗号型”被包围在众多的其他建筑公司的围挡之间。
这个现场和其它现场不同,只有东侧围挡接近马路,其它三个方向根本出不去人,所有我把兵力部署在东侧防线上,每班岗十个人来回游动巡逻。附近村庄里外来人口居多,盗窃案件时有发生,春节期间竟成明抢之势,十分猖獗。我把岗设在外面既是对他们的震慑,也是防止现场内民工跳墙返乡。
现场警卫班班长范昌建匆忙从宿舍跑了过来,敬礼后刚要报告,被我抬手制止。
“你带巡查小组去保安宿舍检查下卫生和人员在位情况。”
“是!”
看着他们走远,我抬脚迈过铁门上的小门,走进了现场。
信步由缰,我背着手溜达走过钟楼、图书室,来到位于现场中间西侧的民工厕所处。
现场内只有这一个大厕所,女厕较小,只有八个蹲坑,男厕较大,有五十个蹲坑,厕所属于临时建筑,上面是石棉瓦,有多个角铁架梁,男女厕中间的横梁离地有近两米高。
我正准备穿过厕所继续前行的时候,忽然听见男厕内传出一声惨叫。
“啊……”
寂静的现场里,突如其来的惨叫声传出老远,令人毛骨悚然。
没等我有啥反应,从厕所里跌跌撞撞跑出三个民工模样的人来,打头的那个赤着双脚、满脸铁青,上身穿着一件破旧的秋衣,浑身上下脏兮兮的沾着屎尿发出一股臭味,刚跑到我跟前,打头的这位就“噗通”摔倒在地。
我急忙上前,蹲下身,拽住他两个肩膀,用力将他翻了个身。
“怎么了?”
民工嘴唇发紫,颤抖着抬起右手,指着女厕的方向,艰难地说了一个字。
“女……”
然后两眼一翻,晕了过去。
两个民工跑上前来,将地上的民工架起,向宿舍方向疾步走去,置我的大声喊问于不顾。
怀着好奇的心情,我迈步进了男厕所,准备一探究竟。
厕所为南北走向建筑,南厕门口有个影壁墙,墙下是转圈的小便池,两米左右进去左转就是大便池了。
大便池分为东西各二十五个蹲坑,横梁上面吊着三盏电灯。虽已是五月,郊区外的夜晚还是比较寒冷,民工随意大小便使得厕所内一片狼藉,卫生纸、报纸、书页、大便到处都是,小便也是流成小河,厕所内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
我站在厕所门口,捂住口鼻,向里面望去。
靠着女厕墙壁东西两个蹲坑的中间位置地上,散落着两只拖鞋和一个旧军大衣。毋庸置疑,肯定是民工爬墙头看女厕里面的人如厕,受到惊吓掉了下来。
女厕里到底是什么东东能把三个状如牛的民工吓成这样?
我放下捂住口鼻的手,侧耳倾听。
厕所内外静悄悄的,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我自嘲地笑了一下。
“人吓人,吓死人啊!看来我是瞎琢磨了。”
就在我住准备转身离开的刹那,忽然。
最里面靠近女厕的电灯泡“啪”地自己碎了。
灯泡碎裂的瞬间,黑暗马上席卷了部分男厕。
紧跟着第二个、第三个灯泡在相隔三秒后相继自爆。
黑暗顺着墙壁、地面疯狂地向站在门口的我扑了过来。
我头皮过电般“嗖嗖”发麻,手和脚不由自主哆嗦起来,想转身而逃浑身上下却使不出半分力气。
就在黑暗吞噬我的瞬间,一股扑面而来的强风把我的制服上衣吹得向后笔直立起,头发整个被吹得向后。一口气没喘上来,仿佛连呼吸都要停止。
眼见我就要挺立不住,黑暗接触到外面的月光,强风嘎然而止。
黑暗中,从女厕方向传来低沉的女人“呜呜呜……”的哭声。
“谁?”
我大喝一声。
哭声依旧。
我紧张的浑身发抖,心脏“咚咚”急跳,后背“嘶嘶”冒着凉气。
身体里冒出一股邪劲,三步合成一步,不到两秒我就窜出了男厕。
站在厕所外面,再立耳倾听。
女人的哭声变成了抽泣,每抽泣一下都仿佛战鼓般打在我的心口上。
去你妈的吧!
我掉转身,脑子里只有一个字。
逃。
赶紧逃离开这诡异之地。
迈开双腿,我沿着空挡平整的硬化水泥路面疯一般向大门方向跑去。
估摸着跑出去有四五十米,眼见前面巡查的兄弟们和范昌建向我这边走来。
刚想放慢脚步。
忽然间我腾空而起,离地面有半米多高,然后重重地摔在地面上,一直向前搓出去有五六米远。
摇摇晃晃站起身,眼前到处都是飞舞的金星星。
撸开胳膊和膝盖。
到处伤痕累累,这一下,把我的左胳膊、两个膝盖有小臂全都搓破了皮,鲜血淋漓。
拨开准备搀扶我的范昌建等人,我转过身向地面上望去。
是什么东西绊的我这样很?
地面上我腾空的地方干干净净,什么阻碍物都没有。
我干!
人多力量大,阳气也重。
我来了精神,今倒要见识下女厕里有什么妖魔鬼怪!
一瘸一拐地,在两个兄弟的搀扶下,我在前面带路向厕所方向走了过去。
径直来到女厕门口,我重重地咳簌了一声。
“里面有人吗?”
无人搭腔,哭声也不见了。
“答话,不然我进来了!”
还是无人应答。
我冲着范昌建挥了下手。
范昌建点了点头,带着两个保安走进了女厕所。
没有一分钟的功夫,三个人走了出来。
看着他们的表情,不用说也知道,里面肯定空空如也。
今晚的事里里外外透着诡异,不弄清楚还真不好说出去,再说了,我说了谁会相信啊?不行,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
就在我准备进入女厕的时候。
忽然从南面离厕所三十米左右远的民工宿舍方向传来一阵惊叫,接着几十个民工穿着裤头的、披着被子的衣冠不整、慌慌张张的向我们这边跑了过来。
我靠!
这要是跑了几十个民工窜回老家,传不传染非典我不知道,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领导肯定轻饶不了我,绝对够我喝一壶的。
再也顾不得厕所事件,我急忙发令。
“范昌建立即集合宿舍人员,通知岗上加强戒备,巡查组每隔半米排开,不准工人跑出去。”
命令刚下达完,弟兄们早已就位。
我浑然忘记了身上的疼痛,上前几步,举起右手,大喊一声。
“都给我站住!”
在部队五年,当了四年的战斗班班长,别的本事不敢吹,嗓门每天都要喊口令练得是刚刚地牛X,别说地方了,部队上全支队没几个敢和我叫号的。
这一嗓子喊出来,旁边的几个保安都禁不住抬手捂住了耳朵。余音滚滚,传出去一里来地。
民工们被我这一嗓子镇住了,前面的立马站住脚步,后面的来不及站脚,撞在前面人的身上,立马滚成一团。
我紧走两步,来到离我最近的一个民工面前。
“怎么了?”
民工一脸惊惧。
“王老五、王老五他疯了!”
支援的二十多个保安急匆匆跑了过来。
“大家都别慌,我是公司的保安主管,你们都站在原地别动,谁是带班的请到我跟前来。”
看见这麽多保安,民工们慌张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站在那开始窃窃私语。
一个四十多岁的民工越众而出,来到我面前。
“我叫张坤,是这个班组的带班。”
“你好!我是公司的保安主管,发生什么事情了?”
“是这样,刚才我们班组有三个民工起夜,回来后其中一个叫王老五的被抬了回来,说是见鬼了,这家伙昏迷了十来分钟,我正准备送他去医院时他忽然醒了过来。抓起瓦刀和大铲见人就砍。多亏他手里的家伙钝,不然不知道要伤几个人呢!”
“现在是什么情况?他住哪个房间?”
“我们是抹灰班的,进了生活区大门左边大一层是我们宿舍。还有,刚才我已经拨了120了。”
我当机立断,安排张坤安抚民工,范昌建维持现场秩序,我带着四个巡查队员走向了生活区。
进了大门,转圈的二层简易楼楼道上、右侧一层房间开着的窗户,挤满了民工正向下面、对面张望,院子里不见一个人影。
我掏出电棍,拇指按在电门上,小心翼翼地带头走进了左侧的民工宿舍。
这小子要是向我挥家伙,先把他放倒再说。
整个房间内上下床铺上空荡荡的,王老五呆坐在靠里面的一张床上,两眼直直地蹬着前方,手里握着瓦刀和大铲,不知道在想什么。
我把拿着电棍的右手放在背后,努嘴示意四个保安出去从两侧的窗户靠近,自己慢慢走了过去。
刚走到中间位置,呆坐的王老五忽然手一松,瓦刀和大铲“当”地一声掉在地上。
他站起身,面向着我的方向,右手抬起,掐了个兰花指,两腿微蹲,左手手心向外掐在腰间,竟唱了起来。
“苏三离了洪桐县,将身来在大街前。未曾开言我心内惨,过往的君子听我言。哪一位去往南京转,与我那三郎把信传。言说苏三把命断,来生变犬马我当报还……”
这一段京剧唱腔被王老五唱得字正腔圆,配合着行云流水的步伐和姿势,把苏三起解演绎的淋漓尽致。
但是在我眼里,这一段唱腔从一个穿着破烂衣服、满脸胡子、又矮又壮的男人嘴里唱出来,用得又是女音,那种感觉要多别扭有多别扭。
张开嘴,“哇”地一口吐了出来。
王老五浑然不知,继续以男人的身体演绎着女人的故事,唱到最后,他身子下蹲,左脚别住右脚,两手向后,抬肘做擦泪状,同时唱了一句。
“我冤啊……”
冤字一出,屋子里房顶的几个灯泡同时自爆,漫天的玻璃碎渣落地的同时,屋里突然弥漫出一股冷气。
冷的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只觉得铺天盖地,刹那间冷遍全身。
黑暗中,我凭感觉发现王老五张牙舞爪向我扑了过来。
不由自主地,我迅速抬起右手,伸向前方,同时用力按住电门。
王老五刹不住身形,直直撞在电棍上,强大的十万伏电流将他击得倒飞出去,“噗通”躺在地上。
在地上抽搐了一分钟,王老五龇牙咧嘴地爬起身又要向我扑来。
此时,从两边迂回的四个巡查保安已翻进窗内,从左右扑上前来死死地按住了他的手脚。
屋子里恢复了正常温度,我蹲下身,将电门前推到强光位置,照向了王老五的眼睛。
王老五的眼睛里眼仁一片死灰,两个黑色的眼珠血一般红。嘴角流着白沫,“嘶嘶”穿着粗气,正努力挣扎。
门口传来急救车急促的鸣笛声。
时间不大,几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匆匆走了进来。
看见眼前的情形,领头的医生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场面,他拍了拍我的肩膀示意我用手电照着他。
打开急救箱,取出针管、安定药水,熟练地敲破瓶盖,吸入药水,推出空气,然后给王老五打了一针。
不到五分钟,王老五安静下来,睡了过去。
四个保安帮忙把他抬上担架,我喊来张坤,让他随行。
在从宿舍往急救车上抬的功夫,我听见民工正在低声议论。
“老五这小子今是咋了?犯得哪门子邪?”
“就是就是,平常三棍子也打不出一个屁的主今咋还唱起戏来了?……”
两天后,王老五生龙活虎地回到了工地,当别人问起他那晚的情况时,他咧嘴憨厚一笑。
“球!老子不就爬个墙头看女人上厕所吗,你们瞎邹啥啊!”
这件事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处理完后为不影响施工进度按照公司要求,我给所有在场的保安开了一个会,要求大家保持沉默,否则按队规处置。
事后第二天,项目部安排人把女厕所拆掉,另建到别处。项目经理亲自带队组织人上香烧纸,折腾了半个晚上。
这件事我同样保持沉默,从未向任何人提起,直至今天。
晓彤鬼故事系列 诡异工地
部分文章源自网友投稿或网络,如有不妥请告知,我们将在24小时内修改或删除。
如果您有故事想与鬼友们分享,请将稿件发送至编辑邮箱:ra216@qq.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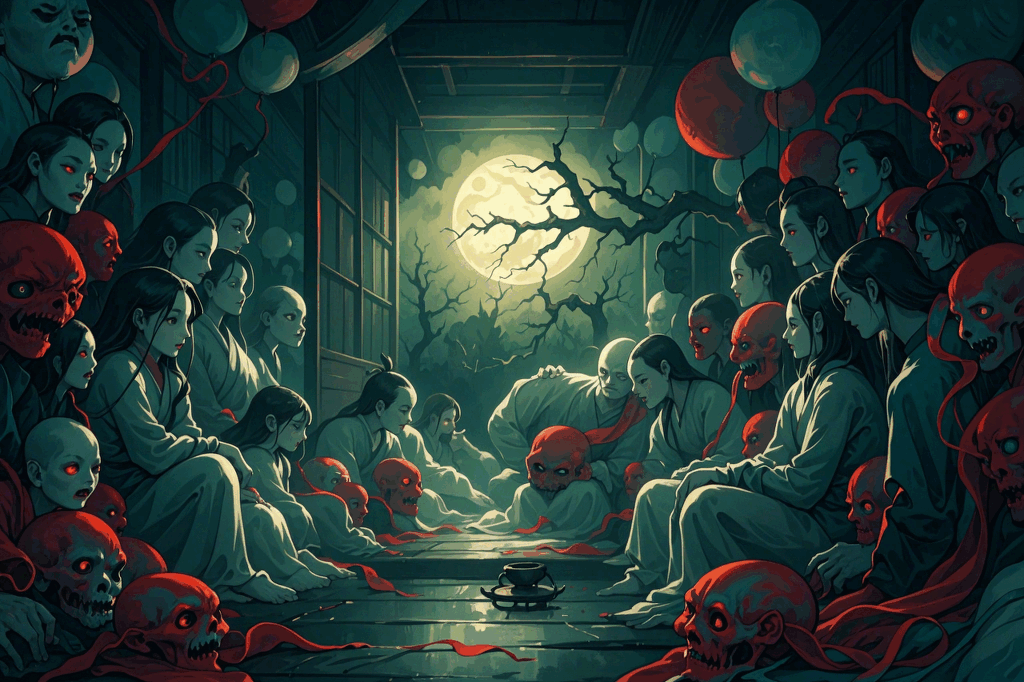
![[短篇怪谈]愚人节的双重陷阱:爱与恨的错位悲剧](https://img.picgo.net/2024/07/13/25283c37dffddc1cf8.jpg)
![[短篇怪谈]酒醉迷路遇狐仙,一觉醒来墓地寻踪](https://img.picgo.net/2024/06/24/22632b794ea9098adc.png)
![[短篇怪谈]家教老师苗谦踏进永生巷514号,遭遇恐怖诡异事件,揭示阴森秘密](https://img.picgo.net/2024/06/24/63a68b3b7c954d009d.png)
![[长篇鬼话]许愿瓶里的诡异愿望](https://img.picgo.net/2024/06/11/3213be784404c75e2c2.png)
![[民间异闻]黄河鬼棺:新婚夫妇亡于冥婚,盗墓贼剖腹产鬼婴](https://img.picgo.net/2024/06/12/3942d64c9c3ad1fbc8.png)
![[短篇怪谈]炕洞秘藏:处女教师的失踪之谜](https://img.picgo.net/2024/06/13/227e3ab6062ef82ede.png)






![[中短篇灵异小说集]23个极短的恐怖小故事](/UploadFiles/2023-08/2/2023082414375073692.jpg)
![[中短篇灵异小说集]经典鬼故事大全](/UploadFiles/2023-08/2/2023082414334270430.jpg)
![[中短篇灵异小说集]八十年代农村灵异事件](/UploadFiles/2023-08/2/2023082414292368407.jpg)
![[中短篇灵异小说集]让人不敢睡觉的鬼故事](/UploadFiles/2023-08/2/2023082414241432785.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