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怪谈之霓虹
2022年03月03日 作者:鬼怪屋 来源:鬼怪屋故事网 短篇怪谈
那个温暖的午后,我躺在病床上,在和煦的阳光里辗转难眠对面的女孩子安静地睡着,枯黄的头发散乱地堆在惨白的枕头上,脸色苍白,嘴唇青紫,那是心脏病导致缺氧的表现。
她躺着,呼吸微弱得让人难以察觉。她像个死人一样。我远远地看着她,觉得那张憔悴的脸似曾相识。我拿起床几上的镜子,镜子中也有一张苍白的脸、一对青紫的唇。不过那双眼还有点神采,眉目间还可以看得到蓬勃的生机。我笑了,是不是得了同样的病,连模样也会变得酷似了昵?
那个女孩儿,我是看着她住进来的。就在今天上午,她被一对衣着破烂的父母送了进来。我看着他们哭泣、下跪、磕头,最后用粗糙的手捧出一大堆破旧的零钱往主治医生的怀里塞。
我叹了口气,怜悯地看着她小小的蜷缩的身体,以及床几上那几个烂得有点酒味的苹果。听说她的心脏病已经很严重了,若不是家境的窘迫,是早该入院的。
我拿了几个苹果,蹑手蹑脚地走到她床前,我走得十分轻,因为我知道心脏病人敏感得可以被一根针落地的声音惊醒。放下苹果,我转身准备去院子里走走。突然,身后躺着的女孩轻轻地说话了。
谢谢。轻得像一声叹息。我红着脸转身:不好意思,吵醒你了。我看见女孩微睁着一双无光的眼,气喘吁吁地准备坐起来。
你睡会儿吧,这个病,是很容易困的。
不了,已经睡醒了,你陪我出去走走吧。她已经穿上了自己那双不成对的拖鞋,一只是绿色的长江七号,一只是粉色的kitty猫,我觉得好心酸。
我叫阿虹。我叫阿霓。我们的手握在了一起。
夜静得不真实,我翻来覆去,只觉得心脏咚咚咚地在胸腔里乱跳。对面的阿霓已经搬到隔壁的准备病房去了,明天就可以做心脏移植,一个匿名的好心人给了她足够的费用。
我忽然喘不上气来,黑暗不断地向我挤压,我哆嗦着伸手,想去按铃。一阵穿堂风吹开了半掩的门,一个黑影无声息地在门口一闪而过,我尖叫一声,本已疯狂乱跳的心顿时不堪负荷。最后的意识里,我隐约听见门外嘈杂的脚步声,如世界末日般让人恐慌。
妈。我睁开眼,全身无力。
你吓死妈妈了,阿虹。你知道吗?你又昏倒了。幸好医生及时为你做了移植手术。你现在已经有了一颗健康的心脏了。快把身体养好哦,你很快就能和正常人一样了。
嗯。我没精打采地敷衍,对这个好消息竟然失去了兴趣。
我忽然想到—个问题:妈,阿霓的手术怎么样?我抓着妈妈的手,掌心沁出薄汗,微微发抖。
你晕倒的那晚,阿霓心脏病发,医生——没能救回她。
我的心,忽然难过得不成样子。床头的相框里,两个模样酷似的女孩身后,正一片阳光明媚。
我走在偏僻的河滩上,鹅卵石光滑冰冷,河风吹着我的脸,我不停地走着。在漆黑的河的尽头,我看见蹲在河边的阿霓。
阿霓阿霓,我好想你!我雀跃地跑过去。阿霓咀嚼着,牙齿沾满碎肉,血流一地。我上前扳过她的肩,你在吃什么?
我的心。
好好吃吗?
苦苦的,苦苦的,我的心,苦苦的。
一声响雷把我从噩梦中拯救出来,雨随着风闯进我的窗子,白色的窗帘扬得老高。我擦了擦额头的冷汗,眼泪不住地流下来。阿霓,是你借梦来看我吗?阿霓,是你还有牵挂吗?
我下床,准备去厨房倒杯水,却感觉到双脚的异样。—个闪电划过夜空,短暂的一秒光明我看清脚上的拖鞋,绿色的七仔和粉红的Kitty邪气地笑着。我尖叫着,失去了知觉。
我无法解释那夜的梦境和那双在我醒后就神秘不见的拖鞋,家里没有人相信我,他们总是把这些归结为我的大病初愈。可是阿霓的影子开始不断地出现在我的世界里,无孔不入。
她会在妈妈买回来的苹果里放上一个烂得有些酒味的苹果;会在我的床头放上一颗她从垃圾堆里找出来的那种不规则的红得似血的玻璃,那是她曾经让我看过她的珍藏,一盒子的那种玻璃,她叫它们玻璃花;我拉开抽屉会看见一颗她为我用柳枝编成的心;甚至她向我形容过的那只没耳朵的秃头猫都会在我家的街角徘徊,瞪着碧绿幽深的眸子,盯着我远去,死死地,死死地盯着我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阿霓给我的提示,她想诉说对我的想念还是发泄对自己薄命的不满?或是她在另一个世界依然凄苦?
我明白,再这样下去,我迟早要疯掉。我绞尽脑汁回忆和阿霓相处的日子,她想要的玩具,她想吃的东西,我——买了回来,一件一件放在她坟前。可是我第二天再去看时,那些东西都被踩成碎片,就像一个不满的孩子拿东西出气一样。我甚至可以想象,在沉静如水的夜晚,阿霓从坟里爬出来,一边气恼我的不解人意,一边用双脚践踏那些玩具和食物。
于是阿霓依然夜夜入梦,夜夜嚼着半颗心,向我说着同样的话:我的心,苦苦的,苦苦的
最后,我决定去看望阿霓的父母。我想那是她真正的牵挂。
一个桥洞里,没有床,只有几张铺在地上的破棉被。一只铁锅里还有半锅杂烩。河风吹过来,刺骨地冷。我让司机先回去,自己坐在一张小矮凳上,看着这一切,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下来。
你是谁?阿霓的妈妈偻着腰出现在我面前。桥洞很暗,我只能看见一个逆光的影子,头发被风吹得很高。我闻到了她身上哀伤的味道。
我我是和阿霓住在一个病房的,我叫阿虹。我站起来,把唯一一张凳子让出来,扶阿霓妈妈坐下来。
谢谢你还来看我。阿霓是我们捡来的孩子,这孩子可怜,医生说,要换心。说得容易,我们哪有钱?好不容易有好心人答应帮我们,可是她又是什么阴性,心源很不好找,等到终于有了心可以换,却又是我们阿霓命不好,没挨到手术就死了。阿霓的妈妈絮絮叨叨,一双昏黄的眼睛盯着我,面无表情,似乎在说着这水长大的吧?
阿霓的妈妈突然笑了起来,呵呵呵——,像有人在拉动一个破风箱。我毛骨悚然,阿姨
她不理睬我,自顾自地呵呵笑着,径直走了出去。
扑通,阿霓的妈妈一头扎进了翻滚着的江水里。我向外跑去,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我不能连阿霓唯一的牵挂都无力保护。腹部一阵翻江倒海地痛,我眼前一黑,不省人事。
我再次醒来已然是三日之后。
妈妈说,阿霓的妈妈因为接连的刺激,神智已经错乱。她在给我喝的水里,下了很多高纯度的氰化物,若不是司机看见有人落水冲进桥洞及时发现了我,我恐怕就再也醒不过来了。
那个女人疯了。你以后别到处乱跑,爸爸很担心的!爸爸抱着我,心疼地说。
可是,她疯了吗?—个疯子可以说出那样有条有理的话吗?一个疯子可以一步步引我喝下毒药吗?她又是在哪里得到的氰化物呢?
自从阿虹手术回来,我就觉得不对劲。
她从医院带回一双破烂的拖鞋,又如获至宝一般藏在床下,我依稀记得那是那个因心脏病突发而死去的女孩的。我知道她们同病相怜,彼此又要好,好到可以以命相换。可是别人孩子的命,怎么及得上自己孩子的呢?我想每个妈妈都会像我一样的。没有阿虹,我的丈夫,也不会再要我这样一个曾经抛弃过女儿的人吧?我只是想要个家,过衣食无忧的生活,这一切,不是我的错。
那晚,我被阿虹的尖叫声惊醒。那声音绝望凄历,像极了那个女孩子临死前的呼号。我和丈夫推开房,看见她惊恐地瞪大眼睛看着穿在自己脚上的拖鞋——她居然穿上了自己带回来的那双破拖鞋——就像被吓破了胆。丈夫忙脱下她的拖鞋,让我拿出去扔掉。我拿着那双拖鞋,整个人都在发抖。
阿虹开始晾恐度日。她常常会从我买的苹果里发现一个烂得有些酒味的苹果,可是我买的每一个苹果都是千挑万选毫无瑕疵的;她会拿着一颗红色的碎玻璃哭着睡去;她甚至告诉我她回家时在街角看见了一只没有耳朵的猫她伏在我耳边,口里吐出热热的呼吸却让我觉得周身冰凉。划说那只猫的眼睛是绿色的,豁嘴巴,牙齿尖利在阳光下闪着白森森的寒光。
我还曾经见她半夜出门,走到那个女孩儿的坟前,然后失控地大哭大笑,把坟前的祭品踩得粉碎。我认得,那些东西都是她白天精挑细选买来的。我只好每夜将哭累后的她带回家,她很乖,只是一直不停地说:我的心,苦苦的,苦苦的
阿虹,你的心苦苦的,那我的心呢?
我想,不是她疯了,就是我疯了。
后来她去见了那个那女孩的妈妈,那个女人居然投毒要她死。我看见她的尸体被从江里捞起来时候,居然还瞪着一双眼。
我无法忘记那双眼。我战战兢兢地度日,直到我把事情告诉阿虹以前所住医院后勤部的小张,她是我多年的好朋友。她说,这种情况在医学上是可以解释的,那一定是因为她移植了别人的心脏,所以就可以看到那个人的生前点滴,最好是让她去见见心脏捐献者的家属。
我把这事交给她,希望一切都可以好起来。
我从手袋里找出一个纸条,上面写着一个地址和一句话,笔迹拙劣,是阿霓的字迹:你的心,我们的心!
阿霓,你是想让我去感谢他们对吗?是他们的儿子救了我。
我找了去。
阿姨开门的是年过半百的女人。
你是谁?女人面无表情。
阿姨,我是阿虹,是您儿子的心救了我。我看着眼前的女人的满头银丝和眼角眉梢藏不住的悲凉凄苦,鼻子酸酸的。
她一侧身,把我让进屋里,屋子里的一面墙上挂着好几张照片,居然,也有我的。阿姨,这是
呵呵呵!女人笑着,像有人在拉一个破风箱,这些,都是活在我儿子的尸体上的人啊,这个女孩子有我儿子的眼睛,这个有肝,这个有肾,还有你,你的心,也是我儿子的!她用枯枝一样的手指狠狠地戳向我的心口,你的心,你的心,是我儿子的!
我哑口无言。
我怎么都不会想到,我的傻孩子居然会在生前就签了什么器官捐献的文件。呵呵呵,他的眼睛还没有合上,他的眼角还有泪,他还有话未说完,他们就把他拉走了。他们把他的肚子剖开,心肝脾胃,一件件地拿出来,明码标价,像市场上的猪肉一般的廉价。没有人知道是谁撞死了他,他走在人行道上,牵着他的女朋友,一辆车把他撞倒了,可是他的女朋友却分毫未损。我儿子的血型很特别,听说当时有两个女孩子都配型成功了,可惜有个女孩手术前死了。
你是说,那两个女孩子的血型都一样?都适合移植他的心?我的心不住地颤抖,全身冰冷。
对!除了你,还有一个叫阿霓的女孩,你该知道你有多幸运了吧。她桀桀地笑。
我逃出那个房子,女人追出来,喷着腐烂的气息,悄悄地在我耳边说:午夜,我总是在你的照片上看到另一个女孩子。她穿着一双旧拖鞋,一只是红的,一只是绿的
像刚从冷水里捞出来,我茫然地在熙熙攘攘的街上走着,我和阿霓的血型我们都可以移植同一颗心脏我们如此相像我们阿霓,是这样吗?那是我们的心?这,就是你要告诉我的真相吗?
阿姨,我我想要一只小白老鼠。我拽着后勤部张阿姨的胳膊撒娇,你去帮我拿一只好不好,就一只
张阿姨长得很漂亮,三十多岁了还是单身。我住院的时候她总是陪我聊天解闷。
你啊!你在这等着,别动我的电脑啊,我在整理最近医院的监控录像,要是出了什么差错,我的饭碗可就保不住了。
放心啦,快去嘛,我要一只大的。我继续周旋,一双眼睛却盯着那台电脑,紧张得发抖。妈妈,你快回来吧,我很不舒服,心跳得好快,好乱。
好,宝贝。
妈妈回到家,她的头发已经没有以前的光泽了,眼角眉梢也染上了凤霜。我今天才发现,原来妈妈已经老了。
妈妈,你还记得阿霓吗?我的眼泪控制不住地流了满面。
嗯,怎么了?妈妈皱着眉头,有些不耐烦,是死了的那个吗?
对!当然是死了的那个!当然!当然就是你吓死的那个阿霓!我再也无法自抑,把手里的u盘扔向她,我知道了,我都知道了!那夜我看见了你,穿着黑衣,装神弄鬼,你吓死了阿霓!你是不是没有想过病房的监视器已经把你照得清清楚楚?!
妈妈的脸色惨白:不可能,不可能,我明明已经不,阿虹,妈妈只是不想你再受苦,你的血型那么特别,是多难得才找到合适的心源,可是院里却说阿霓的病情更重,决定让她先做移植妈妈不想失去你,真的!
不想失去我?你是不想失去我还是不想失去这种富贵生活?你怕我死了,爸爸就会再次不要你。可是你知不知道,阿霓,阿霓是你当年卖掉的那个女孩,是我的孪生妹妹!哈哈,如果当年我不是生了病,卖不出去,恐怕我今天也不会站在这里了。我让私家侦探去查,没想到,却查出这么一个肮脏龌龊的母亲!当年,爸爸突然发迹,你刚生了我们他就喜新厌旧,不要你了。你为了自己以后的好日子,竟然想要把我们卖了换钱。后来爸爸出了车祸,再也不能生育了。他回来找我们。哈哈!你骗爸爸说阿霓病死了。你当时是不是很庆幸还没有把我卖出去?不然爸爸怎么会重新接受你?而被你卖掉的阿霓,在养父母死了之后,就被对乞丐收养了。你没有想列吧,被你卖掉那么些年的女儿,居然让你自己给活活吓死了!
不——妈妈痛苦地抓着自己的头发,冲出门去。
我坐在冰凉的地板上,哭得撕心裂肺。
妈妈死了,死在江里,找到的时候,已经泡得发涨。
半年后。宝贝,爸爸给你找个新妈妈好不好?爸爸说。
好啊,在哪里?顺着他的指引,笑吟吟的张阿姨走过来。
阿虹,以后阿姨可以帮你拿好多白老鼠来玩哦。
我觉得阳光瞬问变得寒冷。我有那么多的疑问:
妈妈应该?就把视频删掉了,为何我却能在电脑里找到?
资助阿霓的好心人是谁?是谁撞死了那个捐心的男孩?
妈妈真的是自杀杀吗?是谁给了阿霓妈妈氰化物?
真的是阿霓指引我找到那个捐心男孩的妈妈的吗?
没有人可以解答。
我真的不能理解,这大人的世界
那个温暖的午后,我躺在病床上,在和煦的阳光里辗转难眠对面的女孩子安静地睡着,枯黄的头发散乱地堆在惨白的枕头上,脸色苍白,嘴唇青紫,那是心脏病导致缺氧的表现。
她躺着,呼吸微弱得让人难以察觉。她像个死人一样。我远远地看着她,觉得那张憔悴的脸似曾相识。我拿起床几上的镜子,镜子中也有一张苍白的脸、一对青紫的唇。不过那双眼还有点神采,眉目间还可以看得到蓬勃的生机。我笑了,是不是得了同样的病,连模样也会变得酷似了昵?
那个女孩儿,我是看着她住进来的。就在今天上午,她被一对衣着破烂的父母送了进来。我看着他们哭泣、下跪、磕头,最后用粗糙的手捧出一大堆破旧的零钱往主治医生的怀里塞。
我叹了口气,怜悯地看着她小小的蜷缩的身体,以及床几上那几个烂得有点酒味的苹果。听说她的心脏病已经很严重了,若不是家境的窘迫,是早该入院的。
我拿了几个苹果,蹑手蹑脚地走到她床前,我走得十分轻,因为我知道心脏病人敏感得可以被一根针落地的声音惊醒。放下苹果,我转身准备去院子里走走。突然,身后躺着的女孩轻轻地说话了。
谢谢。轻得像一声叹息。我红着脸转身:不好意思,吵醒你了。我看见女孩微睁着一双无光的眼,气喘吁吁地准备坐起来。
你睡会儿吧,这个病,是很容易困的。
不了,已经睡醒了,你陪我出去走走吧。她已经穿上了自己那双不成对的拖鞋,一只是绿色的长江七号,一只是粉色的kitty猫,我觉得好心酸。
我叫阿虹。我叫阿霓。我们的手握在了一起。
夜静得不真实,我翻来覆去,只觉得心脏咚咚咚地在胸腔里乱跳。对面的阿霓已经搬到隔壁的准备病房去了,明天就可以做心脏移植,一个匿名的好心人给了她足够的费用。
我忽然喘不上气来,黑暗不断地向我挤压,我哆嗦着伸手,想去按铃。一阵穿堂风吹开了半掩的门,一个黑影无声息地在门口一闪而过,我尖叫一声,本已疯狂乱跳的心顿时不堪负荷。最后的意识里,我隐约听见门外嘈杂的脚步声,如世界末日般让人恐慌。
妈。我睁开眼,全身无力。
你吓死妈妈了,阿虹。你知道吗?你又昏倒了。幸好医生及时为你做了移植手术。你现在已经有了一颗健康的心脏了。快把身体养好哦,你很快就能和正常人一样了。
嗯。我没精打采地敷衍,对这个好消息竟然失去了兴趣。
我忽然想到—个问题:妈,阿霓的手术怎么样?我抓着妈妈的手,掌心沁出薄汗,微微发抖。
你晕倒的那晚,阿霓心脏病发,医生——没能救回她。
我的心,忽然难过得不成样子。床头的相框里,两个模样酷似的女孩身后,正一片阳光明媚。
我走在偏僻的河滩上,鹅卵石光滑冰冷,河风吹着我的脸,我不停地走着。在漆黑的河的尽头,我看见蹲在河边的阿霓。
阿霓阿霓,我好想你!我雀跃地跑过去。阿霓咀嚼着,牙齿沾满碎肉,血流一地。我上前扳过她的肩,你在吃什么?
我的心。
好好吃吗?
苦苦的,苦苦的,我的心,苦苦的。
一声响雷把我从噩梦中拯救出来,雨随着风闯进我的窗子,白色的窗帘扬得老高。我擦了擦额头的冷汗,眼泪不住地流下来。阿霓,是你借梦来看我吗?阿霓,是你还有牵挂吗?
我下床,准备去厨房倒杯水,却感觉到双脚的异样。—个闪电划过夜空,短暂的一秒光明我看清脚上的拖鞋,绿色的七仔和粉红的Kitty邪气地笑着。我尖叫着,失去了知觉。
我无法解释那夜的梦境和那双在我醒后就神秘不见的拖鞋,家里没有人相信我,他们总是把这些归结为我的大病初愈。可是阿霓的影子开始不断地出现在我的世界里,无孔不入。
她会在妈妈买回来的苹果里放上一个烂得有些酒味的苹果;会在我的床头放上一颗她从垃圾堆里找出来的那种不规则的红得似血的玻璃,那是她曾经让我看过她的珍藏,一盒子的那种玻璃,她叫它们玻璃花;我拉开抽屉会看见一颗她为我用柳枝编成的心;甚至她向我形容过的那只没耳朵的秃头猫都会在我家的街角徘徊,瞪着碧绿幽深的眸子,盯着我远去,死死地,死死地盯着我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阿霓给我的提示,她想诉说对我的想念还是发泄对自己薄命的不满?或是她在另一个世界依然凄苦?
我明白,再这样下去,我迟早要疯掉。我绞尽脑汁回忆和阿霓相处的日子,她想要的玩具,她想吃的东西,我——买了回来,一件一件放在她坟前。可是我第二天再去看时,那些东西都被踩成碎片,就像一个不满的孩子拿东西出气一样。我甚至可以想象,在沉静如水的夜晚,阿霓从坟里爬出来,一边气恼我的不解人意,一边用双脚践踏那些玩具和食物。
于是阿霓依然夜夜入梦,夜夜嚼着半颗心,向我说着同样的话:我的心,苦苦的,苦苦的
最后,我决定去看望阿霓的父母。我想那是她真正的牵挂。
一个桥洞里,没有床,只有几张铺在地上的破棉被。一只铁锅里还有半锅杂烩。河风吹过来,刺骨地冷。我让司机先回去,自己坐在一张小矮凳上,看着这一切,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下来。
你是谁?阿霓的妈妈偻着腰出现在我面前。桥洞很暗,我只能看见一个逆光的影子,头发被风吹得很高。我闻到了她身上哀伤的味道。
我我是和阿霓住在一个病房的,我叫阿虹。我站起来,把唯一一张凳子让出来,扶阿霓妈妈坐下来。
谢谢你还来看我。阿霓是我们捡来的孩子,这孩子可怜,医生说,要换心。说得容易,我们哪有钱?好不容易有好心人答应帮我们,可是她又是什么阴性,心源很不好找,等到终于有了心可以换,却又是我们阿霓命不好,没挨到手术就死了。阿霓的妈妈絮絮叨叨,一双昏黄的眼睛盯着我,面无表情,似乎在说着这水长大的吧?
阿霓的妈妈突然笑了起来,呵呵呵——,像有人在拉动一个破风箱。我毛骨悚然,阿姨
她不理睬我,自顾自地呵呵笑着,径直走了出去。
扑通,阿霓的妈妈一头扎进了翻滚着的江水里。我向外跑去,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我不能连阿霓唯一的牵挂都无力保护。腹部一阵翻江倒海地痛,我眼前一黑,不省人事。
我再次醒来已然是三日之后。
妈妈说,阿霓的妈妈因为接连的刺激,神智已经错乱。她在给我喝的水里,下了很多高纯度的氰化物,若不是司机看见有人落水冲进桥洞及时发现了我,我恐怕就再也醒不过来了。
那个女人疯了。你以后别到处乱跑,爸爸很担心的!爸爸抱着我,心疼地说。
可是,她疯了吗?—个疯子可以说出那样有条有理的话吗?一个疯子可以一步步引我喝下毒药吗?她又是在哪里得到的氰化物呢?
人性 怪谈 霓虹
部分文章源自网友投稿或网络,如有不妥请告知,我们将在24小时内修改或删除。
如果您有故事想与鬼友们分享,请将稿件发送至编辑邮箱:ra216@qq.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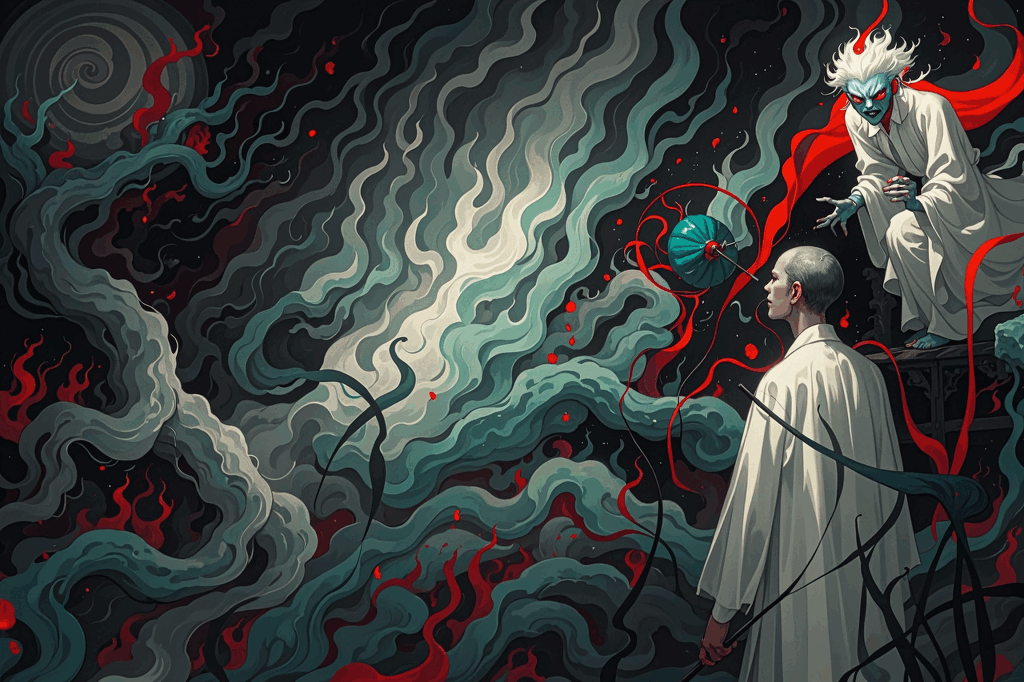

![[短篇怪谈]拖鞋之谜:向阳街的复仇与救赎](https://img.picgo.net/2024/07/22/17-pnga8ea785139185ae6.jpg)
![[民间异闻]月季花下的千年诅咒:翩翩公子与神秘仙子的惊悚邂逅](https://img.picgo.net/2024/06/12/49f27e85bd6f5ba2a5.png)
![[短篇怪谈]鬼窥人](/UploadFiles/2022-12/2/2022122610410812308_S.jpg)
![[短篇怪谈]网恋惊魂:虚拟艳遇背后的恐怖真相](https://img.picgo.net/2024/06/24/50d0066056c2394ea6.png)
![[短篇怪谈]脚朝门睡引灵异事件,风水禁忌解梦魇,惊悚故事揭秘](https://img.picgo.net/2024/07/13/130af45d0c0be9868.jpg)
![[短篇怪谈]末班公交之夜:鬼影招手,血腥惊魂](https://img.picgo.net/2024/06/13/193b3036becc650f30.png)






![[中短篇灵异小说集]23个极短的恐怖小故事](/UploadFiles/2023-08/2/2023082414375073692.jpg)
![[中短篇灵异小说集]经典鬼故事大全](/UploadFiles/2023-08/2/2023082414334270430.jpg)
![[中短篇灵异小说集]八十年代农村灵异事件](/UploadFiles/2023-08/2/2023082414292368407.jpg)
![[中短篇灵异小说集]让人不敢睡觉的鬼故事](/UploadFiles/2023-08/2/2023082414241432785.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