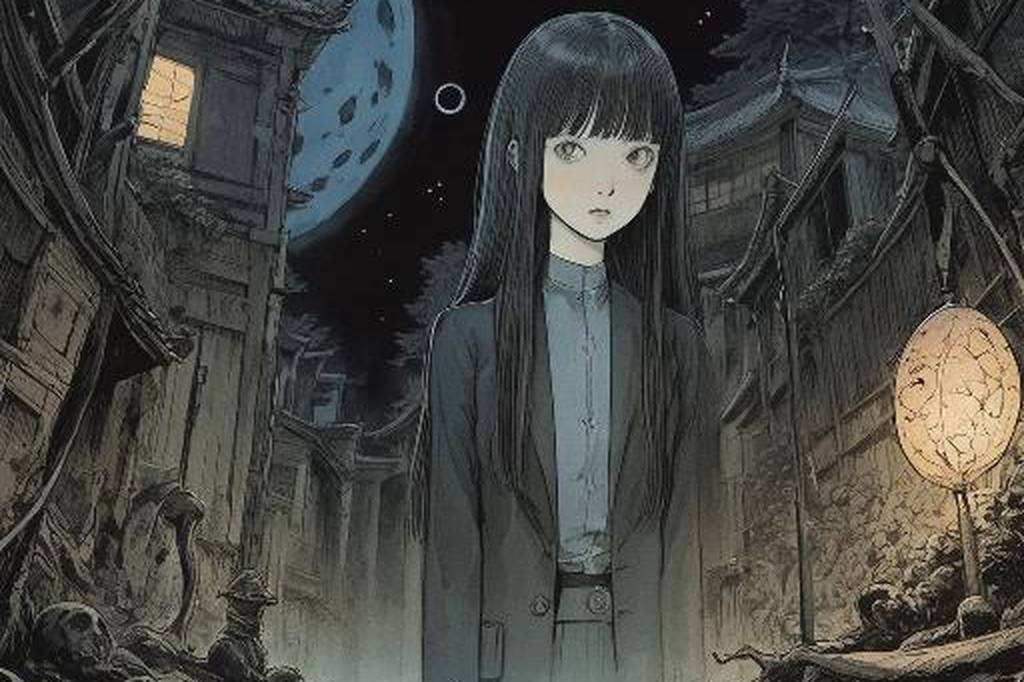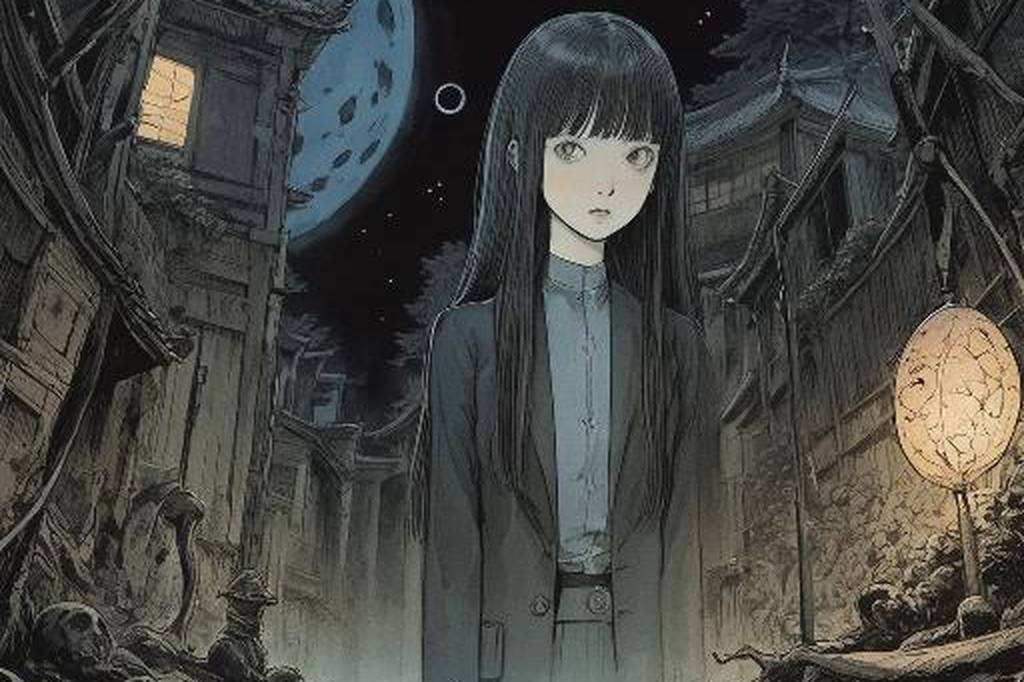
“种瓜的瓜,种豆得豆。”这句古语不知道传承了多少年,似乎一切都是有因才有果么?或许该说什么样的种子,发什么样的芽。
若不是站在眼前的这个颓废男人,我恐怕不会知道这个故事。即便是隔着老远,我也闻见他身上混合着酒臭味和多日不曾清洗的酸味。他随意的将一件皱巴巴地西服套在已经变色的“白衬衣”外,皮鞋已经完全失去了光亮,只有高耸的鼻梁上架着的那副金丝眼镜和后面的那双虽然低垂却依然犀利的眼神仿佛还能提醒我这个男人以前还是过着非常有着优越而高高在上的生活的。
“我出身在一个令人羡慕的家庭。”他使劲舔了舔干裂的嘴唇,我倒了杯水给他,喝完后,他开始谈起那个关于种子的故事。
“虽然是名门望族,却有着外人无法了解的痛苦,无论我们家如何风光,如何显赫,但始终都是单传。
每代下来,都只有一个儿子,每次
家里的长辈总是战战兢兢地抚养这个孩子,即使是以前可以有三妻四妾,但始终只有一个能继承香火的,再要生,要不就夭折流产,要不就是女孩。
人丁兴旺关系到家族兴亡,这是几千来以家族形成个体的中国社会不变的法则,我们家虽然竭尽所能到处寻找办法,似乎也只是徒劳无功,后来想开了,也就算了。
我的父亲是一名富裕的儒商,下海前是大学教授,做生意则一帆风顺,而且又赢得了极好的名声,我从小就在钱和墨水中长大,不过在他的教导下,我没有成为书呆子也没变成尖酸刻薄唯利是图的商人,我似乎平稳地按照家里的为我设计好的路走下去,成为一名外人仰慕的成功者。
但路有时候也会出现岔口。
我娶了一位我非常爱的女人为妻,但结婚六年都没有任何生育的迹象。表面看上去和谐的家庭却始终蒙着一层
阴影,在我看来没有孩子多少有些痛苦,但却不影响我的生活,而双亲则急的满头白发,而这个年代又不必以前可以讨妾,借腹生子我们家更是干不出来。
妻子经常会在睡
梦中流泪,我明白她的痛苦,这也令我更加烦恼,我和她早去过
医院检查,可两人都没问题,妻也一度提出离婚,但被我严厉的拒绝了,如果是为这个事抛弃她,那我就真不是人了。
我的母亲,也是我父亲的大学同学,也是在四十岁的时候才生下我,当时她也是冒着极大的风险,而那之后她的身体也每况愈下,经常腿疼,可是无论什么天气,每个早上她都起的很早。
终于有一次,幼年的我悄悄爬起来跟着看她做什么,我望见她居然在寒冷的清晨披着单衣,走到客厅,手里不知道从哪里拿出一个长形的木制品。
似乎,是一个灵位。
母亲将牌位放在正对客厅的窗口,居然跪了下来。
我刚要过去搀扶其她,但好奇心居然让我躲在一旁看了起来。
母亲居然哭了起来,那声音非常的悲凉。我一时没了没了注意,哭了片刻,母亲站起来,收起牌位回到自己
卧室。
几十年来,母亲天天如此,我始终想知道那牌位是谁的,或许是母亲的好朋友?父亲说母亲年轻的时候交友很广,颇有女中豪杰的味道,而且又是重情重意,如果这样想,只是凭吊一位故友到也说得过去了。
日子在家中窒息的环境下过去,我极力想化解父母对妻子的矛盾,可是三人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直到有一次,父亲居然外出许久,问起母亲,她只是说去了
老家为我讨要生孩子的秘方。
父亲回来的时候非常高兴,仿佛人都年轻几岁,而老两口对妻的态度忽然转变了,反而让我们两人觉得颇为不适应,我以为维持几年的坚冰或许真的打碎了,然后事实证明我错了。
父亲不是一个人来的,他并没有带来什么秘方,儿时带来一个即将临盆的孕妇,父亲说她是乡下的友人,由于家里已经超生,不敢在村子生,所以父亲顺便带她过来,让她在城里生娃,也算帮乡里人做点好事,而且
农村认为就不添丁的家里来个孕妇也可以讨个好彩头,我自然没有怀疑,因为父亲经常帮着家乡人的忙,什么工作调动,资助贫困生之类。
当然我认为这次也不例外,不过这个有着黑红健康脸孔的女人死死地盯着我看,仿佛看怪物一般,接着又看了看妻。她忽然抚摸着自己园滚如西瓜般的肚皮笑起来,那笑容却比哭难看。
我走过去帮她接过行李,但那女人忽然低头摸着肚子对着我小声说着。
“娃啊,记住他。”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但她又重复一遍,我不禁有些纳闷,但看到父亲热情地招待着这个妇人,似乎又和以前对待家乡来的人的态度有些异样,但家里向来是父亲做主,只要父亲不愿说,我从来多问。
两个礼拜后,那妇人生了,是个小男孩,很可爱,不过右手有六指,父亲说没什么大碍。我和妻去医院看她,但她似乎根本没有为人母的开心,却反而是一种非常痛苦的表情,那女人摸着孩子嫩嫩的小脸,又对着我和妻子小声嘀咕着。
“娃啊,记住他们。”
我开始讨厌这个女人了,是的,当时我的确心生厌恶,甚至怀疑这个女人不会把孩子交给我们家里照顾吧,父亲一直都是好人,对他们的要求从来不会拒绝。
但我多想了,没几天,那女人和那孩子都消失了,仿佛从来来过,而父亲忽然劝我和妻去散散心,出去好好旅游。
家里呆的郁闷,我也正想如此,临走前,父亲兴奋地和我告别。
我和妻子去了以前就很想去的地方,这次长期的旅游犹如再次回到蜜月的时候一样,当旅行结束回到家里,我发现居然已经过了一年了。果然玩起来时间过的飞快。
但我没想到奇迹居然出现了,回来一段时间后妻子出现了强烈的妊娠反应,去医院一看居然怀孕了。或许真的是那名孕妇给家里带来了好运,检查后医生还说是双胞胎,当我高兴的将这个好消息告诉父亲的时候,正在沙发上看报纸的他猛的站了起来。
双胞胎?父亲颤抖着声音问我。我觉得他非常奇怪,但没有多想,以为他是开心的有些失态。
父亲低着头,不停地嘟囔着,我隐约听到他在说什么怎么会这样一类的话。很快,他意识到自己的失态,马上堆起笑容,说好事好事,接着失神地走到卧室去了,一边走还一边叹气。由于我也沉浸在即将做父亲的幸福中,居然没有太过在意父亲的变化。
妻的肚子随着时间渐渐隆起,很快就要临产了。
医生告诉我们,妻就会在这几天生了,父亲担心我身体,于是叫我回去睡下,我已经向单位告假,在医院照顾妻很久了,的确有些疲惫,于是,那天夜里我独自一人回家休息,而父母则在医院,有消息就随时通知我。
本来是四个人的家忽然只有我一个人,当然有少许不适应,我并非是个胆小的人,只是那天心里惦记妻,所以总觉得有些心神不宁。
躺在床上无论如何也睡不着,脑子里不知道怎么总是浮现出幼年时候看见母亲对这那牌位祭拜的影子。
好奇心一旦涌起,就如同决堤的洪水。
我开始在家里翻找,终于,在母亲床下的木板隔层里找到了那个用厚厚油纸包起来的灵牌。
当我拆开一看,感到一阵不解。
牌位上赫然写着的,居然是我的名字。当我正在奇怪这牌位的时候,空旷的客厅外忽然传来一阵银铃般的小孩笑声。
我把牌位重新包起放好,走到客厅里。
笑声依然如远处飘来的雾气一般弥漫在冰冷黑暗的客厅里面——出来的时候我发现房子停电了,而这种事情在我家是极少发生的。
跟随着那笑声,我走出了房子,外面比客厅里更冷,北风刮的呜呜的,可还是可以清晰地听到那孩子的笑声。
当我走到屋子外面的庭院角落的时候,笑声开始微弱了,渐渐变成了啼哭的声音,我被这声音搞的无心烦躁,于是想干脆不管了,既然睡不着,不如去医院陪陪妻子。
我正要转身,却感觉到脚底有什么东西在慢慢隆起,仿佛有什么东西在土里蠕动着。
我移脚,慢慢蹲下来,开始用手慢慢地刨开脚底的土。
这个庭院种植了一块草坪,向来是父亲打理的,草长的异常丰茂好看,旁人看的羡慕不已,经常像父亲讨教,但父亲总是闭口不答,不过我发现我脚底的这块土非常的松软,似乎刚翻新不久。
我的手指触及到了什么软腻的东西,如同搁置久了的肥肉,又像豆腐,我急着打开了手机照了过去。
伴随着手机幽暗的灯光,我看到的是一截苍白的手,准确的说是小手,婴孩的小手。
那手有六指。
我已经没有勇气在挖下去了,但是但我要努力支撑起身体离开的时候,我发现那孩子的手紧紧握了起来。
旁边的土开始出现更大的动作,抖动个不停。手机的光也暗淡下来,无论我怎样去按也不再显示。
黑暗里我闻到一股腥臭味,那是土壤中夹杂着腐败肉质的味道,那味道非常熟悉,儿时的我帮父亲翻新土地的时候,经常会找到一些被动物藏匿在土里的吃剩下来的残尸。
有东西顺着我的脚踝慢慢地爬了上来,我的身体如同被绳子绑住了一样,那不知名的家伙居然一直爬到我的耳朵边上,细细地说了一句,那句话虽然微弱,一下就淹没在呼啸的冷风中,但我依然听到了。
‘我认识你。’犹如呀呀学语的孩子说出来的话一样,却根本没让人觉得可爱,话语中没有夹杂任何的生命力。
手记忽然响了起来,我慌忙的接了电话,
身边的一切又消失了,只有脚下的土依旧松软。
电话父亲焦急的告诉我,妻子已经发动了,我胡乱应了声,连忙赶到医院。
焦急地等待几个小时后,当天已经蒙蒙发亮,一名神情疲惫的医生走出了手术室。
‘母子平安。’他勉强地笑了笑。接着揉揉眼睛,伸了个懒腰朝更衣室走去。
可是当把孩子抱出来的时候我发现只有一个。
不是双胞胎么?我抓住刚才那个医生问道,他奇怪地告诉我,只生了一个,并且说这种事进场发生,有很多产妇做的检查都偶尔有失误,双胞胎变一个,一个变双胞胎都是可能的。
既然医生这么说,我也不好在拖着人家,只是看了看孩子。
但是我忽然发现孩子的右手居然是六指。
父亲过来安慰我,说没什么大碍,不影响什么。而我则将孩子交给父亲,自己进去看妻,她很虚弱,不过看得出非常开心,但我却笑不出来,因为我觉得那绝对不是我的孩子。
孩子的六指很快切去了,伤口也好的很快,日子回到了普通而幸福中,当然,除了我,他们三人对那孩子都很喜欢,而孩子也的确十分可爱,我不得不挤出笑容强作开心的照顾那孩子,但那天晚上的事情却如烙印一般让我难以忘记。
在两代人的照顾下,这孩子成长的很快,他继承了家族的有点,漂亮聪明,但他还是多少有些
怪异,他从来不肯叫我爸爸,这让我更加厌恶他,父母和妻经常安慰我,但我却对那孩子更加冷淡起来,聪明的他也知道,从来都是粘着那三个人。
终于,我忍不住了,我把妻子支开,让她带着孩子出去散步,而自己则把父母叫到客厅。
前年那个村里来的孕妇现在怎样了?我直接问父亲,他一听这话犹如遭到电击,身体抖动了一下,我看见他苍老的脸孔和白发,忽然觉得有些不忍,或许我正在触及这个老人心里最脆弱的地方,但一想到那个古怪的孩子,我又硬下心来。
你一定要知道?父亲没有抬头望着我,我嗯了一声。
我不会告诉你的,或者说,只有到我死的那天才会告诉你,那样就算你如何怪我,我也不会知道了。父亲幽幽地说了句,接着拉着同样神情默然的母亲走出了卧室,留下我一个人傻傻地站着。
父母的态度更加让我怀疑,但我表面还是做出一副放弃追查的样子,父亲也仿佛以为我真的不想过多探究。但是很快,我借口出差,来到了老家,虽然说是故土,但其实我根本没来过,只是从父亲那里得知有这么一个村子。
当我来到的时候才发现的确是个普通的在普通的地方,同中国成千上万个村落一样普通,那里的人也一样勤劳朴实,我忽然想到,如果那个妇人根本不是这里的人,我不是白跑了。
不过很幸运,父亲的确来过这里,而且还住在当地一个远方亲戚家里,这个老实的村里人告诉我,他的确知道那个孕妇的下落,并且带我找到了她。
这个女人仿佛知道我会来找她,平和地招待了我,她的家比普通人看过去要豪华的多,已经接近城市的标准了,而且三大件也齐全。
当我把心中疑问告诉她的时候,并且希望看看当年的那个孩子的时候,女人冷笑了下。
你不该问我,孩子的下落应该去问你父亲,当年我只是负责把孩子卖给他罢了,别的我一概不知道,他告诉我你们夫妇没孩子,所以要收养个,我们家穷,什么都没,唯一就是孩子多,一年一个娃,送人的送人,卖的卖,我和我男人根本养不起,有你爸爸这样的富人出的起高价我当然开心了。她如连珠炮一般说着。
可是我没看到那个孩子,我连忙说道,妇人忽然又冷笑了下。
呵呵,想不到他看上去慈眉善目居然也做这个勾当,看来我猜的没错,一个孩子值当不了那么多票子,可怜我的娃,居然做了种子。她的脸上闪烁过一阵嘲讽和悲戚之色,但也只是一瞬间,很快又回到那副冷漠的脸孔。
我不明白地望着她,她见我真的不懂,就继续说道。
生不出娃的家里就是少种子,种什么,得什么,你父亲把我的娃买去做了种子,好让你和你婆娘能生个出来。说完,她站了起来,转过身不再理会我,我还想问什么,却被她回绝了。
离开的时候,我听到房间里响起呜呜的哭声,撕心裂肺。
回家的路上,我想到了关于埋
小鬼的说法——东南亚的赌场之中经常会买来刚出声的婴儿,然后让一些有道行的修士禁锢他们的
亡魂,镇压在赌场之中,为赌场招财进宝,未能生有子嗣的家庭也会偷偷将小孩的尸骸埋在家外墙角,为家里做招财招子的看门小鬼。难不成父亲真的做了那事?我不敢在想下去,只能赶快回家,火车上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见房子外面角落的草坪下有一堆新土,犹如一个坟。
难怪回来的时候草地长的更加茂盛了。我忽然想起有人说过,
死人是最好的肥料,如果一块地上的花草长的很好,那下面一定埋了人。
到家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又是个懒洋洋的秋日下午,快到家的时候,我看到那孩子一个人站在庭院里玩耍。
他真是我儿子么?或者还是那个种子结出来的果子?我的脑子乱得很。
我猛的生出一种想过去抱他的冲动。阳光照在那孩子光滑如缎般的脸上红扑扑的很好看,他挥舞着像藕节样的手,仿佛在跳舞一样。
当我慢慢走过去,却看到高高伸展的手上,在阳光下显的有些异样。
我清晰看到原本被切去的六指好好的长在那伤口上,仿佛在嘲笑我的愚蠢一般。
孩子背对着我,他迎着太阳落下的常常黑影正好叠加在那个土堆上,土堆又开始耸动起来。我站的地方离孩子只有十米远,却宛如相隔天涯。
土堆中伸出的小手抓着孩子的脚踝,但孩子仿佛什么也感觉不到,那双手也是六指,却已经腐烂接近白骨。
我再也无法忍受了,那就是我儿子,我不允许任何东西抢走他,我扔下衣服和行李,冲过去抱起他,亲着他的小脸。
‘我认识你。’怀中的孩子忽然说道,话语和那天晚上听到的一模一样,他不安分地从我手里挣脱出来,冷冷地望着我。
‘我认识你,而且我把你的孩子吃掉了。’他哈哈地笑了起来,那笑容分外熟悉。
就像那个村子里的女人。孩子笑完后就晕了过去,我抱着他,看了看那手,又成了正常的五根手指。
父母和妻吓坏了,还好孩子很快又醒了过来,只不过依然躲着我。
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在也无法人兽了,于是我拿出翻新草地的工具跑到外面。父亲仿佛知道我要做什么,猛的朝我冲了过来。
不要啊,他老泪纵横的拉着我的手臂,曾几何时这双手是那么强壮有力,但现在却如此软弱,我几乎感觉不到他的力量。
‘爸。我一定要解决这事。’说完,我将外套脱掉,大步走到外面对这那土堆挖起来。
父亲瘫倒在地板上,而母亲也尖叫着跑过来想阻止我。
‘你会后悔的!一定会!’母亲如疯子般
诅咒着我,披头散发的样子非常可怕,我瞟了眼妻,她流着泪抱着孩子,她从来不不会阻拦我任何事情,在她眼里,我是永远是对的,绝对不会犯错的,就像父亲在母亲心目中一样。
只有那孩子,却咬着指头带着嘲笑和好奇的眼神望着我。
随着工具的翻动,草坪支离破碎的翻开了,果然,我找到了那个深埋的婴孩,虽然四肢开始腐烂,但脸部依然清晰可见,我小心的把那孩子的
尸体拿出来。
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我扶着那孩子的脑袋,喃喃自语到。
当我将尸体缓缓脱离泥土的时候,忽然发现似乎被什么扯到了,低头一看,原来婴孩的脚踝处居然还有一只手,一只只剩下骨头的手掌死死的抓着尸体的脚踝。
居然有两具尸体?我回望母亲,她面无表情地望着我。
接着拂去面上的泥土,腐败之气更加严重。那下面是一具稍微小点的尸骸,似乎已经掩埋很久了。
我讲两具尸体都拿出来,用白布盖着放在草地上,阳光冷了下来,妻中小家伙一直盯着那尸体。
回到屋子里,妻和我坐一边,父母坐对面,在灯光下他们仿佛一下苍老了几十岁。
‘第二具尸体是谁?’我问他们。
‘你的孪生哥哥。’母亲低声说,我忽然震惊了,我何时有个哥哥?
‘我们家族向来只能有一个传接香火的后代,而不管如何,我们的家族都是生双胞胎,而其中一个就要作为镇宅和保护家族的兴亡而必须要活埋在家里的后院,绝不能有两个男丁同时存在,而且埋下去就不能再开启出来,否则家必败,你以为这些财富地位是怎么来的?那是你的兄弟,我的兄弟,你
爷爷你祖爷爷的兄弟的命换来的,或者说,这本省就是一笔交易罢了。’父亲忽然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
‘你一直没有后代,我非常着急,所以从那个妇人处买了个孩子,我想你一定也知道了,同样,我把那孩子活生生埋了下去,造孽啊,多好的孩子,我只是希望作为种子可以让我们家开枝散叶,或许可以改变这该死的命运,但没想到还是双胞胎,但生出来却又只是一个,我实在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
每一个活下来的男丁,都会沿用死去的兄弟的名字,表示已死一次,不会在被世间的命格所牵绊,当然可以做任何事情都一帆风顺。‘父亲地垂着头,我很难相信一向被外人称道善良富有爱心的父亲居然会杀死一个襁褓之中的婴儿。
而这一切却又都是为了我。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母亲要去祭拜那个牌位,为什么那个牌位上的名字和我的名字一样。
我到底是谁,只是一个借着已经死去的兄长的名字活下去的人么?
‘家败了,家一定败了,罢了罢了,这样或者本身就太累了。’父亲忽然站了起来,摇摆着身体走了出去。
母亲一言不发,只是转身回到卧室,出来的时候拿着那个牌位。
那天晚上,我们把那两具尸骸和牌位都烧掉了,火光中我儿子的样子变的非常痛苦,并且大病了一场,病好后父亲的生意也开始一落千丈,我的工作也丢了,上个月,两人先后过世,相隔不到一个星期,仅存的财产也用于为他们操办后事了。
现在的我只能靠着妻子微薄的收入支撑家用,当然,我还在一直找工作。“男人忽然开心起来,我很难想象一个人从高出跌落到谷底,经历这些事情还能笑出来。
“不过我很高兴,因为我儿子终于开口叫我爸爸了,有了他,做任何事情都有动力,我会一直努力下去的。”说完,他这才拿出自己的资料。
忘记说了,他是来报社招聘的。我有好的接过来,并告诉他最好收拾一下,下午再来见社长。他兴奋地走出去,临走前还热情的给了我个拥抱。望着他的背影我觉得对他来说,得到的远比失去的要多得多。(种子完)